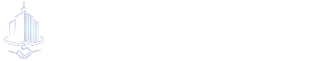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来电)和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街电)的专利侵权纠纷已成为近年来共享充电宝行业风起云涌大背景下的“别样风景”。从深圳到北京再到广州,来电握着6件专利将街电从南诉到北,再诉到南,为阻止街电继续扩大市场规模,来电的策略也是不断加码,诉讼、行政投诉、申请禁令等招数悉数使出,街电因此陷入诉讼漩涡。
其中,来电近期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申请的针对街电的诉中禁令,已成为双方纠纷的焦点,并在业界引起大量关注。
8月27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来电的禁令申请举行了听证。在听证过程中,来电和街电主要针对关于被控侵权产品侵犯来电专利的可能性、行为保全的必要性、行为保全的担保等焦点问题进行了辩论。
关于被控侵权产品侵犯来电专利的可能性,双方针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了当庭对比,陈述了各自的意见。来电认为被控侵权产品完全落入其专利保护范围,街电则认为凭肉眼可视就可以看出被控侵权产品并未落入来电的专利保护范围,或者至少还需要经进一步审理、进行比较复杂的技术对比才能作出判定。
关于行为保全的必要性,来电主要认为“若街电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铺设被控侵权产品,即便法院判决街电立即停止侵权,但执行将由较大困难甚至无法执行”、“铺设充电设备的速度是衡量共享充电宝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制止被控侵权产品的铺设行为对于专利权人乃至整个共享经济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若因使用被控侵权产品导致用户体验受损,将给共享充电行业造成灾难性影响”、“如果不及时制止侵权行为的扩张,将导致申请人丧失因专利权获得的竞争优势”。
针对来电的观点,街电则认为: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存在而不合理地迟延寻求司法救济时,可以认为没有保全的必要性。来电在全国范围内起诉街电专利权侵权案件达30余起,涉案专利的侵权诉讼早已在深圳和北京展开,时间跨度长达近2年,来电在这些诉讼中均没有提出行为保全的要求,可见来电长期以来自身也认为没有行为保全的必要性。
2、根据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相关在先判例指引,若权利人的声誉没有被侵害,或者损害赔偿可被准确计算,且被申请人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赔偿,则没有保全的必要。街电目前现金流充足,此次两个诉讼中来电的赔偿请求只有200万元,街电完全有能力支付。
3、来电以同样的专利提起的诉讼即将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开庭二审,故街电产品是否侵犯来电专利权,近期内将会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来电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不争取在一个诉讼中解决与街电的侵权纠纷,反而在努力“多点开花”,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滥用诉权的恶意十分明显,不仅增加了街电的诉累,也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权威和效率。
4、街电并非因为使用了来电专利而不当侵占了来电的市场份额,也并未因为使用了来电专利而逼迫来电降低产品价格,事实上,根据涉案证据,来电自身的产品也未应用其专利,街电提供产品的收费标准比来电高。
5、涉案专利为共享充电设备的内部构造,一般消费者难以感知,消费者并不会因为该特定的内部构造而特意选择街电产品,来电自身提交的证据中也证明用户选择共享充电宝的考虑因素中不包括设备的内部构造。
6、共享充电市场有很多家服务商,来电的市场份额极小,即使不颁发禁令对来电也不会产生扩大损失。而街电市场占有率大,颁发禁令显然有悖于“颁发禁令给被申请人带来的损失应小于或相当于不颁发禁令给申请人带来的损失”这一标准。
关于行为保全的担保,来电表示愿意提供200万元某保险公司保函作为担保,街电则表示根据来电在该案中的主张,街电的市场规模过亿,来电提供的担保远远低于街电可能遭受的损失。此外,街电还表示,如果法院认为需要,街电愿意提供足额反担保,反担保金额可以超过亿元。
目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尚未裁定是否准许来电的禁令申请。
近年来,结合知识产权案件诉讼周期长、审理程序繁琐、判赔额与当事人预期相差悬殊等情况,以及相关法院对“加多宝”案、“中国好声音”案、“稻香村”案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作出了禁令裁定,知识产权案件的当事人因此也会在自身的案件中考虑采取向法院申请禁令的方式向竞争对手施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6日公布了《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有消息称,该司法解释将会于近期正式公布实施,其中的规定也得到了学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其正式实施后势必将成为行为保全司法实践的重要保障。
结合该背景,笔者就禁令的法律依据、禁令的申请及准许条件等问题咨询了两位法学专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瑞介绍,在我国现行法律中,首先规定“禁令”制度的,是我国在加入WTO之前,于2000年修改的《专利法》,该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此外,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及《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也有相关规定。
2013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则是我国首次确立行为保全制度,该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孙国瑞还表示,诉中禁令具有依附性的特点,必须依附于诉讼。在诉讼开始后,一方当事人(一般为原告)为了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可以向法院申请诉中禁令(包括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禁令时,必须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依法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而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担保的方式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等,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包括现金、房产、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等。人民法院则会根据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是否会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是否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考虑是否准许当事人的申请。如果申请人因为申请有错误而给被申请人造成了损失,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案件中,错误申请禁令损害赔偿责任属于严格责任,无论申请人有无过错,错误申请禁令造成被申请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也就要求申请人在法院的担保金额应足以弥补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宗玉表示,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民事侵权案件中,如何在诉讼过程中进行行为保全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执行。根据该规定,民事侵权诉讼过程中的行为保全应当包括4个条件,其中对“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及“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其行为保全申请”这两个条件的审查和界定最为关键。对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的相关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当事人一方基于主观的故意而产生行为(如故意转移资产等)或其他的客观原因(如经营失败等),最终的结果体现在其败诉的判决难以执行(资产被转移造成执行不能)或造成当事人其他的损害(除专利侵权之外可能对专利权人的人身权、物权或其他财产权造成损害)。对于担保,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法院都会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而且大部分行为保全案例中,法院会要求担保人提供足额的财产担保。
此外,《民事诉讼法》第104条还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这是对财产保全的担保解除作出的规定,所以有观点认为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有所区别,不能等同适用。这里要注意到,《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的就是财产保全,而行为保全是在财产保全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扩张,其权利基础还是财产权利,脱离财产的范围,行为保全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行为保全中,也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04条的规定由诉讼当事人提供担保予以解除,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类似案例。
附:《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第八条 【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七条规定的难以弥补的损害是指被申请保全行为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通过金钱赔偿难以弥补或者难以通过金钱计算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认为属于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一)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或者持续,将抢占申请人的市场份额或者迫使申请人采取不可逆转的低价从事经营,从而严重削弱申请人的竞争优势的;
(二)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或者持续,将会导致后续侵权行为的难以控制,将显著增加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的;
(三)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将会侵犯申请人享有的人身性质的权利的;
(四)被申请人无力赔偿的;
(五)给申请人造成其他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认为不属于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一)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存在而不合理地迟延寻求司法救济;
(二)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申请人无合理理由未使用或者实施相关知识产权且未计划使用或者实施的;
(三)被申请保全行为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比较容易通过金钱计算的;
(四)其他不会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对于造成将来的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申请人其他损害的认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对于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认定。
其中,来电近期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申请的针对街电的诉中禁令,已成为双方纠纷的焦点,并在业界引起大量关注。
8月27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来电的禁令申请举行了听证。在听证过程中,来电和街电主要针对关于被控侵权产品侵犯来电专利的可能性、行为保全的必要性、行为保全的担保等焦点问题进行了辩论。
关于被控侵权产品侵犯来电专利的可能性,双方针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了当庭对比,陈述了各自的意见。来电认为被控侵权产品完全落入其专利保护范围,街电则认为凭肉眼可视就可以看出被控侵权产品并未落入来电的专利保护范围,或者至少还需要经进一步审理、进行比较复杂的技术对比才能作出判定。
关于行为保全的必要性,来电主要认为“若街电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铺设被控侵权产品,即便法院判决街电立即停止侵权,但执行将由较大困难甚至无法执行”、“铺设充电设备的速度是衡量共享充电宝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制止被控侵权产品的铺设行为对于专利权人乃至整个共享经济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若因使用被控侵权产品导致用户体验受损,将给共享充电行业造成灾难性影响”、“如果不及时制止侵权行为的扩张,将导致申请人丧失因专利权获得的竞争优势”。
针对来电的观点,街电则认为: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存在而不合理地迟延寻求司法救济时,可以认为没有保全的必要性。来电在全国范围内起诉街电专利权侵权案件达30余起,涉案专利的侵权诉讼早已在深圳和北京展开,时间跨度长达近2年,来电在这些诉讼中均没有提出行为保全的要求,可见来电长期以来自身也认为没有行为保全的必要性。
2、根据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相关在先判例指引,若权利人的声誉没有被侵害,或者损害赔偿可被准确计算,且被申请人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赔偿,则没有保全的必要。街电目前现金流充足,此次两个诉讼中来电的赔偿请求只有200万元,街电完全有能力支付。
3、来电以同样的专利提起的诉讼即将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开庭二审,故街电产品是否侵犯来电专利权,近期内将会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来电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不争取在一个诉讼中解决与街电的侵权纠纷,反而在努力“多点开花”,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滥用诉权的恶意十分明显,不仅增加了街电的诉累,也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权威和效率。
4、街电并非因为使用了来电专利而不当侵占了来电的市场份额,也并未因为使用了来电专利而逼迫来电降低产品价格,事实上,根据涉案证据,来电自身的产品也未应用其专利,街电提供产品的收费标准比来电高。
5、涉案专利为共享充电设备的内部构造,一般消费者难以感知,消费者并不会因为该特定的内部构造而特意选择街电产品,来电自身提交的证据中也证明用户选择共享充电宝的考虑因素中不包括设备的内部构造。
6、共享充电市场有很多家服务商,来电的市场份额极小,即使不颁发禁令对来电也不会产生扩大损失。而街电市场占有率大,颁发禁令显然有悖于“颁发禁令给被申请人带来的损失应小于或相当于不颁发禁令给申请人带来的损失”这一标准。
关于行为保全的担保,来电表示愿意提供200万元某保险公司保函作为担保,街电则表示根据来电在该案中的主张,街电的市场规模过亿,来电提供的担保远远低于街电可能遭受的损失。此外,街电还表示,如果法院认为需要,街电愿意提供足额反担保,反担保金额可以超过亿元。
目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尚未裁定是否准许来电的禁令申请。
近年来,结合知识产权案件诉讼周期长、审理程序繁琐、判赔额与当事人预期相差悬殊等情况,以及相关法院对“加多宝”案、“中国好声音”案、“稻香村”案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作出了禁令裁定,知识产权案件的当事人因此也会在自身的案件中考虑采取向法院申请禁令的方式向竞争对手施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6日公布了《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有消息称,该司法解释将会于近期正式公布实施,其中的规定也得到了学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其正式实施后势必将成为行为保全司法实践的重要保障。
结合该背景,笔者就禁令的法律依据、禁令的申请及准许条件等问题咨询了两位法学专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瑞介绍,在我国现行法律中,首先规定“禁令”制度的,是我国在加入WTO之前,于2000年修改的《专利法》,该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此外,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及《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也有相关规定。
2013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则是我国首次确立行为保全制度,该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孙国瑞还表示,诉中禁令具有依附性的特点,必须依附于诉讼。在诉讼开始后,一方当事人(一般为原告)为了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可以向法院申请诉中禁令(包括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禁令时,必须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依法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而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担保的方式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等,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包括现金、房产、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等。人民法院则会根据申请人胜诉的可能性、是否会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是否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考虑是否准许当事人的申请。如果申请人因为申请有错误而给被申请人造成了损失,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案件中,错误申请禁令损害赔偿责任属于严格责任,无论申请人有无过错,错误申请禁令造成被申请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也就要求申请人在法院的担保金额应足以弥补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宗玉表示,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民事侵权案件中,如何在诉讼过程中进行行为保全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执行。根据该规定,民事侵权诉讼过程中的行为保全应当包括4个条件,其中对“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及“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其行为保全申请”这两个条件的审查和界定最为关键。对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的相关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当事人一方基于主观的故意而产生行为(如故意转移资产等)或其他的客观原因(如经营失败等),最终的结果体现在其败诉的判决难以执行(资产被转移造成执行不能)或造成当事人其他的损害(除专利侵权之外可能对专利权人的人身权、物权或其他财产权造成损害)。对于担保,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法院都会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而且大部分行为保全案例中,法院会要求担保人提供足额的财产担保。
此外,《民事诉讼法》第104条还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这是对财产保全的担保解除作出的规定,所以有观点认为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有所区别,不能等同适用。这里要注意到,《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的就是财产保全,而行为保全是在财产保全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扩张,其权利基础还是财产权利,脱离财产的范围,行为保全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行为保全中,也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04条的规定由诉讼当事人提供担保予以解除,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类似案例。
附:《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第八条 【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七条规定的难以弥补的损害是指被申请保全行为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通过金钱赔偿难以弥补或者难以通过金钱计算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认为属于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一)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或者持续,将抢占申请人的市场份额或者迫使申请人采取不可逆转的低价从事经营,从而严重削弱申请人的竞争优势的;
(二)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或者持续,将会导致后续侵权行为的难以控制,将显著增加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的;
(三)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将会侵犯申请人享有的人身性质的权利的;
(四)被申请人无力赔偿的;
(五)给申请人造成其他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认为不属于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一)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存在而不合理地迟延寻求司法救济;
(二)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申请人无合理理由未使用或者实施相关知识产权且未计划使用或者实施的;
(三)被申请保全行为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比较容易通过金钱计算的;
(四)其他不会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对于造成将来的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申请人其他损害的认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对于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认定。